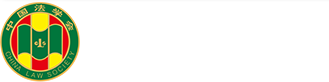自從“藥家鑫”案以來,“激情殺人”一詞便進(jìn)入了社會(huì)公眾的視線,司法界和法學(xué)理論界圍繞這個(gè)話題的爭論也未停止過。隨著江哥被害案的開庭審理,“激情殺人”又一次被提了出來。所謂激情殺人,按照學(xué)理上的解釋,它是一種本無任何殺人故意,但在被害人的刺激、反抗之下而失去理智,失控而將他人殺死的行為。對于激情殺人的行為,我國的刑法上并沒有明確的規(guī)定,相關(guān)的法學(xué)教科書上似乎也是語焉不詳。然而,翻開中國古代法典,激情殺人的行為卻是赫然在列,只不過它有一個(gè)專屬的罪名——故殺。
集中國古代法典之大成的《唐律疏議》中,對殺人行為從法理上進(jìn)行了區(qū)分,具體劃分為謀殺、故殺、斗殺、誤殺、戲殺、過失殺等六種殺人行為。誤殺即誤殺傍人的行為,也就是刑法理論上說的打擊對象錯(cuò)誤;戲殺是在嬉戲時(shí)殺傷他人的行為;過失殺則是在缺乏高度注意或異常謹(jǐn)慎的情況下發(fā)生的殺傷行為,不完全同于今天的過失殺人;謀殺類似于今天的故意殺人,是指二人或二人以上,事先有所準(zhǔn)備,共同謀劃的殺人行為。如果是一人獨(dú)自所為,但事先經(jīng)過了周密計(jì)劃和充分準(zhǔn)備,也按謀殺對待;斗殺即斗毆?dú)⑷说男袨?也就是今天所說的傷害致死。但什么是“故殺”呢?現(xiàn)今的一些相關(guān)書籍都將“故殺”解釋為“故意殺人”,但從《唐律疏議》的解釋來看,是“非因斗爭,無事而殺”,即罪犯與被害人之間事先并無利害沖突而將其殺死的行為,似乎又不同于今天所說的故意殺人。那么,“故殺”究竟是什么樣的行為呢?
其實(shí),在唐朝時(shí),就對什么是“故殺”的問題產(chǎn)生過爭論。從法律上說,故殺與斗殺的主要區(qū)別,就是故殺在主觀上有殺人的故意,而斗殺在主觀上并沒有殺人的故意;故殺同謀殺的區(qū)別在于故殺并沒有殺人的預(yù)謀,而謀殺是有殺人的預(yù)謀。顯然,故殺的殺人故意,不是蓄謀已久的,而是臨時(shí)產(chǎn)生的。這就非常符合今天所說的“激情殺人”的要件了。
明代的律學(xué)家在編注《大明律》時(shí),給“故殺”的行為作了一個(gè)注解:“臨時(shí)有意欲殺,非人所知曰故?!逼渲械年P(guān)鍵就在于“臨時(shí)有意欲殺”。對此,清初的王明德在他的《讀律佩觿》一書中就認(rèn)為:故殺的行為“雖未為有心欲殺于平日,而實(shí)則有心欲殺于臨時(shí)”,“或因先被其傷重而倖之,或恐其復(fù)起相毆也,而更毆之,以期必至于斃焉,是則斗毆中之故殺也?!痹诖?明確指出了故殺的基本要件,以及同斗毆?dú)⑷说膮^(qū)別:殺人的故意是臨時(shí)產(chǎn)生的。與王明德同時(shí)代的沈之奇在《大清律輯注》一書中也指出:“臨時(shí)有意欲殺,非人所知,此十字,乃故殺之鐵板注腳,一字不可移,一字不可少?!币虼?在“欲殺”即產(chǎn)生殺人故意這一點(diǎn)上,區(qū)別于斗毆?dú)⑷?;在“臨時(shí)”這一點(diǎn)上,又區(qū)別于謀殺。所以從行為構(gòu)成要件來看,故殺同今天所說的“激情殺人”是基本一致的。從量刑上看,故殺行為比斗毆?dú)⑷艘?但又比謀殺要輕,正是考慮到了其中具體情節(jié)的差異性。
在清朝的案例匯集《刑案匯覽》中,就記載了這樣兩起故殺的案例:
一起是江西張旺發(fā)糾毆故殺劉鹿仔身死案:
“張旺發(fā)因攔阻劉鹿仔割伊魚塘之草,被劉鹿仔趕毆,該犯起意糾毆泄憤,邀同堂弟張新德等互將劉鹿仔毆跌倒地。劉鹿仔辱罵,該犯起意致死,用刀將劉鹿仔連戳斃命……張旺發(fā)依故殺律擬斬監(jiān)候?!?br />
另一起是宿州民朱瑞山糾毆故殺尤學(xué)成身死案:
“朱瑞山因向尤學(xué)成索討賭欠被罵,糾曠保等將其毆扎倒地。該犯被罵忿極,頓起殺機(jī),用刀扎傷其囟門(腦門)等處,立時(shí)殞命,實(shí)屬故殺,合依故殺者斬監(jiān)候律擬斬監(jiān)候,秋后處決?!?br />
從這兩起案例來看,都是由于斗毆引發(fā)的。在此之前,兇犯并沒有殺人的故意,而是在爭執(zhí)斗毆的過程中,遭被害人辱罵,惱羞成怒,臨時(shí)起意將被害人殺死,顯然是屬于“激情殺人”。所以官府在定罪時(shí),既沒有按照“謀殺”,也沒有按照“斗殺”,而是按照“故殺”來定罪,這應(yīng)當(dāng)說是科學(xué)合理的。
當(dāng)然,由于故殺較多地發(fā)生在斗毆的場合,大多是在斗毆或爭執(zhí)過程中臨時(shí)起意將人殺死,而斗毆又大多是群毆,如上面兩起案例,都是群毆?dú)⑷说?因此,如何準(zhǔn)確定罪、合理分擔(dān)刑事責(zé)任無疑是一個(gè)非常重要的問題。在這兩起案例中,殺人者是臨時(shí)起意,而幫兇者并不知情,所以在定罪量刑上是有差異的?!皬埻l(fā)糾毆故殺劉鹿仔身死案”中,幫兇的張新德等人并沒有殺人的故意,所以是按照“共毆案內(nèi)余人本律辦理”的規(guī)定,僅處以杖刑;“朱瑞山糾毆故殺尤學(xué)成身死案”中,幫兇的曠保等人因人數(shù)較多,所以是按照“結(jié)伙三人以上持械傷人不分首從”的規(guī)定,發(fā)配云貴兩廣極邊煙瘴充軍,同樣沒有按照“故殺”定罪。
古代法律關(guān)于故殺的規(guī)定,揭示了“激情殺人”的構(gòu)成要件,對于科學(xué)合理地處理相關(guān)行為提供了可資借鑒的經(jīng)驗(yàn)。